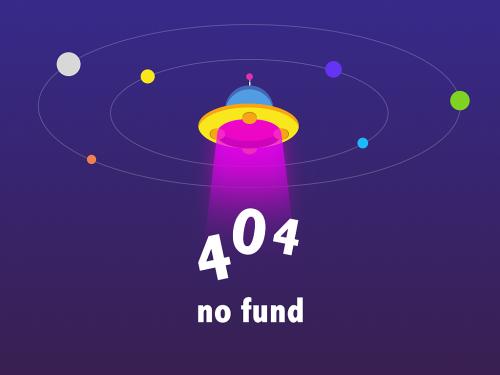梅贻琦 – 国学网-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
字号:字月涵
生卒:189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
时代:民国
籍贯:天津
简评: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189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梅贻琦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
生平简介
梅贻琦(189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著名教育家,字月涵,天津人。1909年考取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914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工学士学位。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梅贻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1962年逝世于台北。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校长”。其夫人韩咏华,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梅贻琦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诵: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出长清华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华校长,可称得上受命于危难之时。自罗家伦于1930年离职(当属被逐)后,清华长时期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连续空缺了11个月,不断易人,反复被逐。国民党政府只好令在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出山。梅贻琦感到荣幸、快慰,但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虽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的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1940年9月,梅贻琦的美国母校邀请他参加校庆,并颁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丢不下艰难竭蹶中的联大,没有前往。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为渡危艰,当时清华的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通过为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以改善教职员生活。梅贻琦将该社所获的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拥戴。
1948年时局发生变化,是年底梅贻琦与一些名教授被当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国民政府要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梅坚辞。据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教授回忆,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表示:他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这“表现了学人的风格,树立了师德的典范。”“不愧是个‘人物’。”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因他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后,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上。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民主治校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延揽人才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永远的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依然属意教育。
梅贻琦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文章分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