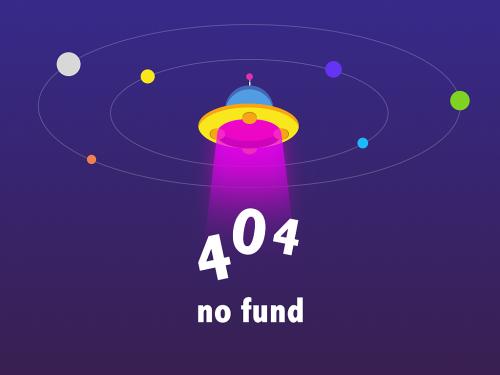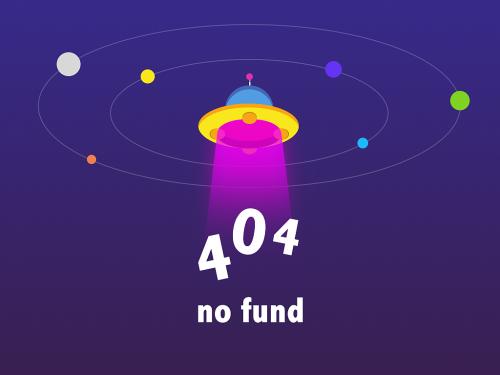重新发现沈从文的精神轨迹——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
1981年夏,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寓所。
《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 张新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文史学界,传记研究是个易于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一本有分量的传记,往往要依托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史料会迫使研究者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找寻更为恰当的阐释话语。但传记研究也是一个易于“媚俗”的领域,把一个人塑造成某种理念的坚守者,远比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容易得多,就像张爱玲分析《海上花列传》时提到的,“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往往更符合人们对传记的期待;那些“平淡而近自然”的作品则易于为读者摒弃。从这个层面上来讨论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一书,这本着眼于传主的生活、思想层面的传记,在写法上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
一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本著作充分利用了沈从文生前未发表的400多万字的资料,主要是各类杂文物研究成果及书信和日记。如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都较为明晰地讲述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这对我们了解他的精神轨迹颇有帮助。自然,这些漂亮的文字经过了理性的筛选,不利于我们重构当年的历史场景。于是,张新颖试着引入沈从文亲友的回忆,以增强叙述的质感:如1969年底,沈从文去咸宁干校前夕,在家收拾东西,满屋狼藉。张允和来看他,要走时,沈从文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信,似哭似笑地说,这是妻子张兆和给他的第一封信。当张允和问是否可以看看时,他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又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再也不出来了……”张允和正觉得好笑,沈从文却“吸溜吸溜”地哭起来。这一哭,使得整个叙述顿有活色生香之感。
张允和的回忆提供的恰是沈从文自己觉得不必强调的部分。试想,一个老男人行将被发配远方,体弱多病,妻子不在身边,而单位又无意回护,被搬家时的琐碎磨得筋疲力尽,也真的算是哭告无门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时候哭鼻子天经地义。当年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陈乔回忆说,运动中沈从文的情绪不稳定,常哭,担心自己发病,身上随时带有写着单位和名字的小牌子……此类琐细,生活气息十足,思之令人五味杂陈。毕竟时代很大,个人很小,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独立思想与时代相对峙,更似故事而非实景。每个人的直接对手其实都是生活本身。有些人对于政治风向较敏感,而另一些人则较为迟钝。但时代的风云变幻会引起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这些变化打乱了中国知识者在穷达之际的回旋余地,让他们无所适从。
二
沈从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在生活轨迹上颇有相似之处。年轻时在北平和上海,一边流着鼻血,一边写作;中年后,则在各类运动的颠沛流离中,一边哭着鼻子,一边做杂文物研究。在对那些运动进行评判之前,我们不应低估的倒是这个湘西人生命的韧性,以及他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风度:在创作界,他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好作家之一;而学术上,他开启的名物研究,影响深远,至今追随者甚众。中国失去了一个好的作家,但获得了一个好的学者,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更为重要的是,杂文物研究本身就是沈从文的志趣之一,他在抗战期间就已广为涉猎。在建国后的学科划分中,选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依托,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此前无论金介甫,还是凌宇的沈从文传中,都提到他在创作上有不断跃升的趋势。上世纪40年代后期,沈从文的创作有日益浓重的哲学化倾向;在形式上,他似乎在用文字去展现某种情绪的体操——这种努力发展的极致实则是音乐。张新颖也在文中特意写了沈从文在“文革”前夕,尚在夜深人静时听西方古典音乐的情景。当他对文字的锻造达到某个顶点后,则需要找寻一个新的领域来安置自己的热情。从这个角度讲,即使沈从文在创作上并未封笔,他恐怕也很难遏制自己对杂文物研究的兴趣。
我们无意为当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辩护,但既然是传记研究,我们着眼点首先应是传主生命的发展和完善;而非相反,用人物去给某种历史评价模式做注。无论是张新颖的传记,还是解志熙等学者近年来所做的史料考辨,都注意到沈从文在1948年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中,政治批判只是诱因,更为直接的则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因素。但郭沫若的点名批判、文代会的冷落,以及沈从文本人所经历的极端状态,很容易让我们按照政治抵抗的方式来进行解读。当前,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转折时期的研究在文史两界都是热点,对于此易代之际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不应蜕化为古代文学中的“遗民文学”研究。诸多现代知识分子在民国期间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民国具有它的特殊性。前期的军阀割据,使得中央政府处于一种较弱的状态;而此后所从事的抗战,更让国家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相对松散。新中国建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这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调试与此政权的关系,在其领导下进行文化工作,是他们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因为,任何一个统一的政权,都会和现代知识分子有此磨合过程。学术和国家密切联系,受后者的制约和引导,实际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从沈从文突然去世、而错过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马悦然确认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去假设,如果他一直写下去,又会取得多大的成就。张新颖教授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本书中,他没有把沈从文新中国后转向杂文物研究简单地处理为一个悲剧,也没有像若干“某某的最后多少年”那样,把一个人后半生的价值局限于他对前期信仰的坚守上,而是试图去讲述一个现代知识者努力调试自己,在新的领域再出发的故事。张新颖在这本传记中将沈从文对学术、对业务的执着刻画得异常动人。沈从文其实是一个有着出色的政治敏感和讨论热情的人,但他很少会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去夸夸其谈。执着于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一点沈从文比同时代的很多人看得要清楚,也比后辈研究者中的很多人要诚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